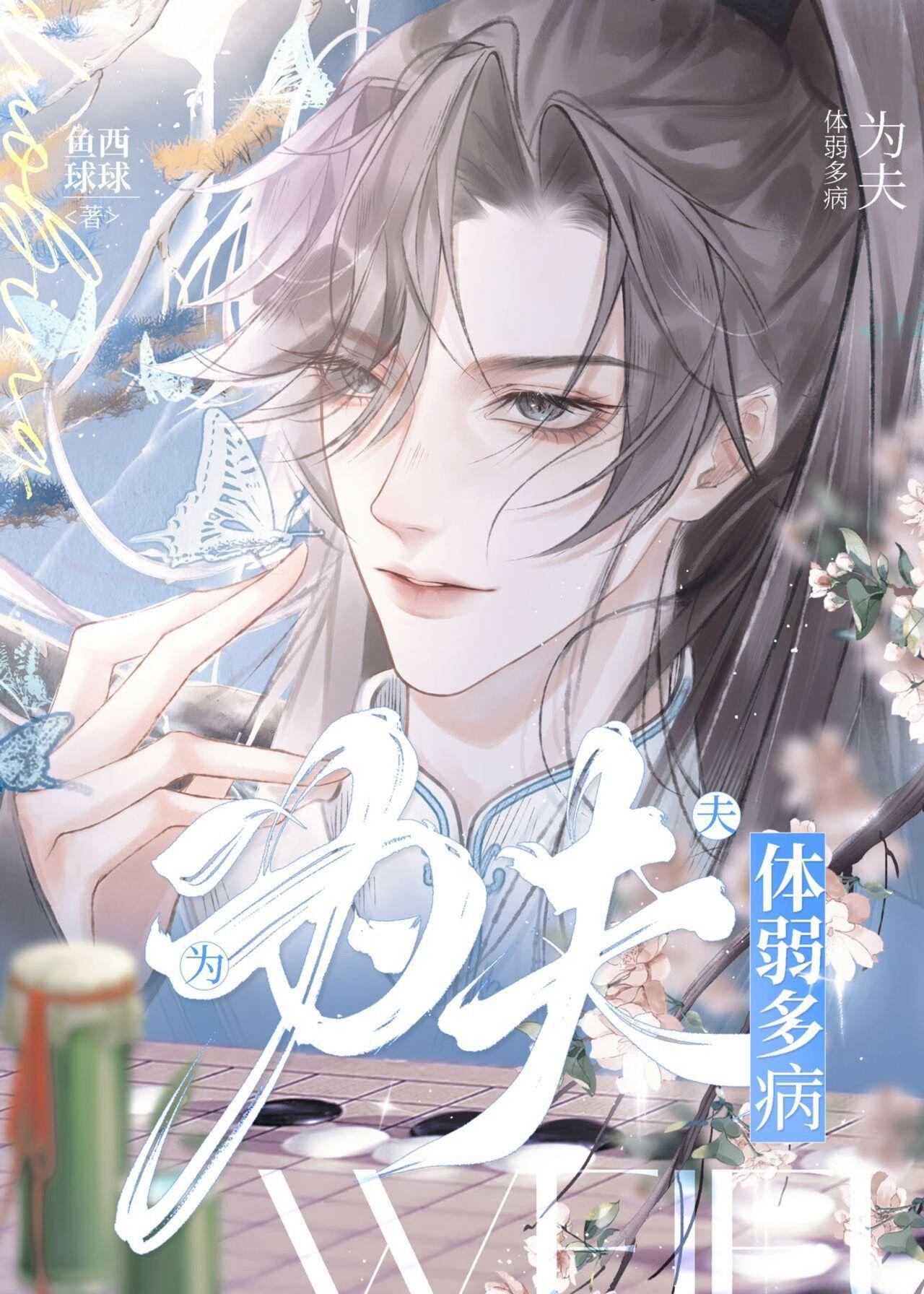八点看小说网>深圳明天有日落吗 > 第210章(第2页)
第210章(第2页)
秋泓轻轻一动,胸腹前就是一片撕心裂肺的疼,他只能摇摇头,用气声回答:“别动。”
祝时元见此,一动也不敢动,他直愣愣地躺着,直到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。
“秋相,你,你是不是流血了?”祝时元惊叫道。
秋泓这会儿才攒够爬起身的力气,他喘了两口气,答道:“不是我。”
“不是你,难道是……”祝时元一凝,因为,此时此刻,他那适应了黑暗的眼睛已能借着头顶缝隙中透出的一点微光看见,正对着自己的那面墙上用人的血肉粘出了无数密密麻麻的人名,而这些人名,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那就是姓吴。
“吴鹤,吴观,吴申,吴阔,吴少和,吴……”祝时元张大了嘴巴。
秋泓顺着他的视线看去,只见在那由血肉写成的人名中,赫然在列一位自己无比熟悉的旧识。
不,不仅是旧识,还是恩师,至交,故友。
吴重山。
明熹八年(一)
吴重山是长靖十五年入的仕,彼时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,就被长靖皇帝祝旼钦点成了丁卯科的榜眼。
他仕途顺风顺水,先是入翰林院做编修,而后就顺理成章地进了礼部,没过几年,又被祝旼提拔入东宫任讲官,成了沈惇和秋泓之前最年轻的长缨处大臣。
长靖三十六年,北牧南下,他带着一众翰林们致仕,又不偏不倚地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清贵的声名。以致明熹八年,朝中几党斗得难解难分时,不得不把他请来,主持公道,肃清朝纲。
那时的吴重山三推四脱,倒叫人觉得,他是真的取舍两难,无可奈何才出仕任职的。
这年初春,吴重山入京那日,他的老朋友裴松吟特地出城迎接,就连日日被太子拴在宫里出不了门的秋泓都得了空,随着裴松吟一起,来到揽镜山下,等候他的老师。
当年三番两次舍弃秋泓,并在背后处处给“南党”使绊子的裴松吟如今已过六十五,朝中请他告老还乡的声浪越来越大,尤其是沈家的那帮姻亲,叫得尤其来劲,恨不能明日就把裴松吟逼得请辞。反倒是都察院安生得很,竟没趁着这关头,跟随沈淮实一起落井下石。
裴松吟心里明白,这是秋泓给他留着面子,嘴上却不肯服软,他坐在车里,直挺挺地等着秋泓来前面拜见,却连帘子都不肯掀开看一眼。
“师相。”秋泓规规矩矩地叫道,“昨日学生在东宫,听裴侍读说,师相您风湿病犯,坐卧不宁。正巧前些日,学生母亲从老家来京,家乡有一名医随行,据说此人最擅针灸,等哪日师相得了空闲,学生请那位老先生上裴府,为师相纾解一二。”
透过那一道窄窄的缝隙,裴松吟看到了秋泓立在马前的身影,他沉着脸,不说话,给坐在自己身侧的家仆使了个眼色。
家仆心领神会,下车回道:“秋先生的好意,我家相爷心领了,只是府中名医也不少,就不劳烦秋先生了。”
秋泓淡淡一笑,不以为然,他一拱手,客气道:“既如此,那学生就不叨扰师相了。”